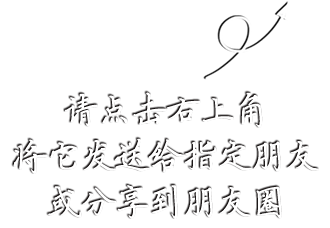■ 子 安
病中的日子,像泡乏了的旧茶叶,在医院的白色里浮沉,没滋没味,心里头也总像硌着点什么,毛毛刺刺的。窗台外头,几株野菊倒活得自在。就那么挤在墙根缝里,黄是黄,白是白,小朵小朵的,开得没心没肺。风来了,它们点点头;雨落了,它们抖抖身子。也不管有没有人看,就那样安静地吸着气,吐着气,把日子过得平平展展。
医院后墙那片爬山虎,长得可真叫一个疯。绿啊,泼辣辣地漫了一墙,叶子叠着叶子,密得透不过风。远看,真像一道绿瀑布,哗啦啦地从墙头淌下来。风一过,叶子就“沙啦沙啦”地翻腾,挨挨挤挤,热闹得很。蝉声藏在浓荫里,“知了——知了——”,断断续续,没完没了。刚听着烦,像有根小针在心上戳。可听着听着,那绵长的调子,倒像把小针磨钝了,心上的褶子,仿佛也被这声音一点点熨平了些。你说这声儿打哪儿来?像是从地底下拱出来的,又像是从老早以前的光阴里漏下来的,轻轻巧巧,就滑过了心坎。
那天下午,日头懒洋洋地晒着。我踱到后院,一眼就瞧见个老人,弓着背,蹲在杂草堆里。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褂子,头发花白得像落了霜。他正捻着几根草茎,手指头枯瘦,动作却轻得很,像是在跟草拉家常。他觉出动静,扭过头来。脸上沟沟壑壑,可那笑容,温暖得像晒暖了的棉絮。
“小伙子,看草呢?”他嗓子有点哑,像风吹过干芦苇。
我嗯了一声。
他举起手里几根不起眼的草,递到我眼前:“认得这是啥不?”没等我答,他自己就絮叨开了:“草啊,跟人一样,各有各的命,各有各的时辰。急不得的。时候到了,芽就冒出来;时候到了,花就开出来;等到该枯了,入药了,那也是它修来的功德。”他下巴朝墙根抬了抬,“瞧见那野菊没?没人疼没人爱的,霜打一打,那股子清苦味儿反倒正了,是味好药引子呢。”他说着话,空气里就飘着一股清冽的、带点微苦的草香,丝丝缕缕,钻进鼻子,又溜到舌尖上打个转儿。
老人的话,像山涧里的小溪流,不急不缓地淌。“天地万物,都有自己的步调。人心要是乱了,毛了,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找不痛快。心要是能定下来,像这些草啊木啊似的,安安稳稳地,这草木的光阴,就是顶顶好的药了。”阳光正好落在他脸上,那些皱纹的褶子里,像是盛满了日头和草木一起酿出来的、沉甸甸的光。
我站在那儿,一时没言语。目光扫过院子深处,猛地就撞见了那棵老槐树。半边身子叫雷劈过,焦黑焦黑的一个大口子,狰狞地咧着,像道永远好不了的疤。可你瞧那疤边上,竟又倔强地抽出了新枝子,一簇簇鲜嫩的绿,蓬蓬松松地往上蹿。它不吭声,不抱怨那场大难,也不急着向谁显摆它多能扛,就那么沉默着,按着自己的老主意,一寸寸地长,长成了自己的一幅画,沉静里透着筋骨。
阳光穿过头顶密密的枝叶,碎金子似地洒下来,落在泥地上,也蹦到我脚背上,暖烘烘的。树影子在风里轻轻晃悠,时间好像也走慢了,像温水,无声无息地漫过脚面,把心上的皱褶一点点熨平。四下里真静。只有风溜过叶子的“沙沙”声,偶尔几声鸟叫,清脆得像小石子儿掉进深水潭里,“咚”一声,漾开一圈圈静悄悄的涟漪。那些盘在心口的焦躁,病痛带来的烦闷,不知不觉,就被这草木一呼一吸的声儿,给一点点化开了,融进了这片安安静静里。
活在这世上,谁不是风里来雨里去?谁的心上没沾过灰,没落过霜?可你瞅瞅这天地,看看这些不言不语的草木,它们自有股子坦荡劲儿:该怎样就怎样,不拧巴,不较劲。草木在光阴里喘气儿,荣了枯,枯了荣,自有它的道理。人心要是能寻着这份安稳,那些个烦扰,也就真像浮尘一样,手一掸,就散了。
远处传来药碾子“咕噜噜”滚动的声音,沉沉的,闷闷的。早先听着只觉得枯燥难熬,这会儿听来,倒像是大地沉稳的心跳,一声声,透着一股子老旧的从容。草木循着它的节气,该荣时荣,该枯时枯;人心要是能顺溜了,万物都养人。原来那些苦药汤子的涩,只要心静了,也能咂摸出大地深处藏着的那一点慈悲的甜味儿来。
心平,是九月的蒲草籽,不声不响,不争不抢,只悄悄落进土里,等着自己的春天。那疗人的方子,哪有什么秘传?它就摊在每一片叶子舒展的懒腰里,刻在每一圈树木不紧不慢的年轮上,藏在这草木荣了又枯、枯了又荣的悠悠光阴里。只等一颗清清亮亮、安安稳稳的心,去听,去看,去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