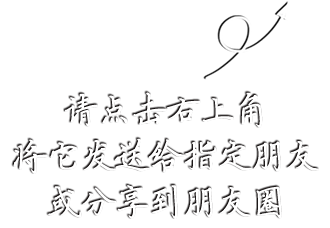■ 杨松华
在依稀的晨光里,祖父祖母、父亲母亲起床了,在我们家前屋后屋急促地走动、小声地说话。他们在忙着我们家“高”年猪前的准备。
“高”,在家乡人心目中意味着最在上之称,热烈、盛大。“杀”是家乡人在过年时最禁忌说的话。用“高”年猪来代替“杀”年猪,那是对自家年猪的敬畏。也是年猪对这年的最神圣的奉献。
那时,虽然生活清贫,可家家还是要尽最大努力养一头大肉猪到过年“高”。如果到过年时,没有“高”一头猪,那这个年的质量将要大打折扣。
祖父祖母、父亲母亲轻手轻脚地做事、交谈,他们不想惊动猪圈内的那头猪。此时,他们个个神情肃穆、不苟言笑,养了一整年的猪将要在下一刻杀身成仁,主人自然于心不忍。人畜之间也是有感情的。
尽管四个大人把说话、做事的“音量”放得最低,我还是早早在这边床上醒来。每到年的节骨眼上,孩子们的心情都显得特别激动,不像平日,总要在大人的千呼万唤中才肯起床。跟我同睡一床的二弟也在那头醒了,他从被窝探出小脑袋一会儿看我,又一会儿侧耳听屋那边的动静。他知道今天我们家“高”年猪。二弟小我三岁半,他还不会自己穿衣服起床,需要妈妈帮他穿。妈妈正忙得热火朝天,一时三刻顾不上他。我把他哄进被窝重新躺下。
灶屋,烟雾昂扬、热气弥漫,祖母和母亲正在用三眼灶台中靠里边最大的一口“老天锅”烧开水。水开得咕噜咕噜冒热泡,祖母还在往灶内填柴。这一“老天锅”开水,马上要用到煺猪毛,所以水要烧老到,多沸腾几次,待年猪一放“红”,就用两只水桶把开水盛过去,倒进烫猪盆。
祖父种田,也是做泥匠的手艺人。他还有一门匠艺,会杀猪。每年到春节,祖父都会和邻村的一个男人做搭档,给邻近村庄的农户家“高”年猪,赚些过年费。
祖父和父亲,还有那个搭档男人也来了,他们已经在前屋晒坪上摆开了阵势。本来,我们家也可以在后院“高”年猪,后院隔墙就是猪圈,放猪出来也方便。偏偏每一年都要把猪弄得高嚎着、人也累得生拉硬扯着,放到前屋晒坪上“做事”。我不知何故,问祖父。祖父说:“‘高’年猪要响众,要让村人看到。”原来,我们那乡下有传统,哪一家“高”完年猪,要请村人吃一顿年猪饭。放在明亮处“高”年猪,让村人看到,这家在“高”年猪,等会儿要去他家吃年猪饭。如果放在后院,放在偏僻处“做事”,怕被村人误会,这家人不想请村人吃年猪饭。
祖父和他的搭档男人,还有父亲就可以架猪“做事”,祖母和母亲自然在准备年猪饭。吃年猪饭,当然以家中新宰杀的这头猪为主菜肴,每桌一大钵猪血汤,一大盘红烧肉,一大碗肥肉细条汤,至于猪肝、猪肚、大肠,都用来炒、爆、焖、焗、煮,外加上其他到过年时节才可以吃上的腐竹、木耳、香菇、粉丝,搭配上自家菜地种的这时节出产的胡萝卜、大白菜等,一桌丰盛的菜肴就呈现在前来吃年猪饭的村人面前。
祖父他们已经提绳索往猪圈走。我自觉躲得远远的,却被母亲喊过去,她让我现在就去外公家,请外公一家人都来吃年猪饭。我知道家里人已经提前跟外公家打了招呼,让他们今早来我家。可农村的礼节还是要过的,母亲这是让我去陪着外公他们来。我老大不情愿,他们这时哪有空去,自然落到我这大孩子头上。
外公家不远,两里路,我小跑着就到了。今年,除了做剃头匠的大舅一早出门剃头,顺带收账,其他人都来了,快坐满两桌。慢悠悠地走路,我都急死了。想回家把猪尿泡吹起来。猪尿泡得带着猪体内的热气好吹起来,冷久了,就吹不起来了。
每一年“高”年猪,我们小孩最高兴的事就是有猪尿泡玩。猪尿泡吹起来后,不易破,可以当球踢着玩。
我一路想着,我家的年猪理到什么程度,那猪尿泡是不是被做搭档的男人在理猪内脏时,随手扔垃圾桶里了。当我陪着外公一行人到家时,年猪早理好了,祖父正用清水洒扫晒坪,父亲在忙着一家家跑,请村里人来我家吃年猪饭。从屋里飘出一阵阵的菜香,我咽了下口水,先不管了,我也不再陪外公他们进屋。我奔向祖父,大喊:“猪尿泡!猪尿泡!在哪儿?”
祖父瞪起眼儿,骂:“真不懂事,去陪外公他们坐!”
我几乎要哭出腔儿,冲祖父喊:“我要猪尿泡!”
“喏!在那儿。”祖父只得停下洒扫,指向屋檐下。我这才发现,那儿悬挂着一只吹起来的大大的猪尿泡。
每年都是这样,在小年前的两三天,村里人家就开始“高”年猪。然后一家家的,都请去吃年猪饭。年的序幕就在一家家的请吃年猪饭中拉开。
我摘下猪尿泡,再也顾不上吃年猪饭,邀上几个小伙伴,踢猪尿泡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