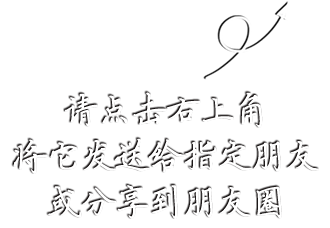■ 张 勇
当木门在五月的风里吱呀作响时,我被满院的白撞得眼眶发酸。那丛在青砖黛瓦间静默了三十载的栀子,又在旧时光里绽成了雪。
老祖母的簪子还别在妆奁深处,银饰上的珐琅早已剥落。她常说旧时姑娘晨起梳妆,总爱摘朵带露的栀子别在鬓边,任那抹甜香随步摇轻颤。如今迁居县城后的每个雨季,街角总传来悠长的叫卖声。竹筐里的栀子裹着湿润的毛巾,像被小心珍藏的月光。卖花阿婆的蓝布衫上洇着汗渍,却总不忘提醒:“要斜斜地插在白瓷瓶里,清水漫过花茎三指,这样香气才绵长。”
高考那年的栀子开得格外盛大。我们在香雪海里填写志愿表,钢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,与花瓣飘落的簌簌声应和着。三十年后再读刘禹锡的诗,忽然懂得“色疑琼树倚”的惊艳里,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悸动。那个总在图书馆角落读书的少年,他的白衬衫上是否也曾沾过栀子的芬芳?
1995年的毕业季,省城的梧桐叶在烈日下蜷缩成问号。宿舍空荡的床板上,汽水渍早已凝成褐色的泪。我最后一次擦拭窗台上的积灰,突然发现玻璃上还留着去年冬天呵出的雾气画成的笑脸。门关合的瞬间,二十岁的蝉鸣被永远锁进了门框的阴影里。
如今每当栀子暗香浮动,我总想起杨峰歌里唱的“幸福像花儿一样”。或许真正的青春从不会褪色,它只是化作一缕香魂,栖息在记忆的褶皱里。当霜雪爬上鬓角,我仍会在某个清晨,从泛黄的信笺间抖落一片花瓣,让那年夏天的纯白,重新绽放在苍老的掌纹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