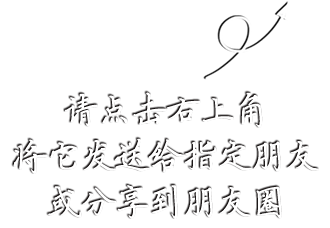■ 朝 颜
七月似火。要说不热,那当然不够真实。
但总有人能在无边的暑气中寻得一份清静和自在,比如我。很负责任地说,我在夏天使用空调的频率和时长远低于多数城市居民。扪心自问,撇开身材胖瘦不说,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乐观自持和安稳笃定起了作用。
我是个天性乐观的人。这要感谢基因对我的厚待,还有父母多年给予的言传身教。童年时,夏天于我是最快活的时光:到村头的小河里戏水撒欢,爬到屋后的老榆树枝干上睡午觉,取蜘蛛网粘在长竹竿上捕知了……我们不知道世上有电风扇,更不知道还有空调这个词,我们有的是鹅毛扇、棕叶扇、蒲扇、纸扇。午后,老人们坐在厅堂里讲古,讲着讲着,渐渐都沉入静寂,总有一两把扇子从谁的手中滑落下来。
其实,快活的背面还有艰辛的暑日劳作。夏收夏种是一年中最关键的时节,要想活命,谁也不能对土地轻慢。我家劳力少,父亲是电影放映员,母亲承担了田里和家里的大部分事务。虚岁六岁,别的孩子还在撒娇耍赖,我的童年就宣告结束,开始了下地劳作的时光。
但我们家的劳作和别人家很不一样。在烈日下,我们戴着草帽,躬身田亩,母亲总是耐心地教我,稻秧怎么拔、怎么捆扎,秧苗怎样莳入水田。我几乎从没见过她在田间露出愁眉苦脸的表情,更没听过她对天气有丝毫抱怨咒骂。她愉快地领受命运和季节给予的苦和累,仿佛一切本该如此、天经地义。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劳作的场景常常收获路人由衷的赞美,他们尤其爱赞美个头矮小的我,六岁,竟然已经会莳田了。许是受母亲影响,那时候我几乎没有热和难受的概念,我常常连草帽都丢在一边,以至烈日在我脸上留下永远的印痕。
有父亲参与的劳作则更为快活。最热的天里,我们一家在旱地里种红薯。挖地、开沟、埋苗、撒肥、盖土、浇水,再以蒿草或灌木枝叶遮盖,大人干重活,小孩干轻活,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。父亲一边挥锄,一边就开始讲笑话了。他是个极有才华的民间段子手,善于从方言俚语、日常生活中挖掘素材,槽点一句一句爆出来,句句都能押上韵。我和哥哥也没闲着,适时插科打诨、加入创作。于是我们所在的那块地便充满了欢声笑语,炎炎的烈日早已被抛诸脑后。路过的和不远处劳作的村民们见了,都说我们一家就像在说相声。
如今想来,贯穿一生的幽默感和乐观精神大约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埋下了种子。父亲难道不热吗?他打赤膊的时候,我见过他背上的汗珠,有玉米粒那么大。他穿的衬衣,只要出个门,回来就全湿透了。所谓“心静自然凉”,更多是一种从容面对的心态占了上风吧。
参加工作以后,我自然不需要再下地劳作。父母也转了身份,成为城里人。但从前的精神降温法,始终没有被我们丢失。教书年代,我最爱练字。一边听音乐,一边临帖。写毛笔字,也写钢笔字。其时学校条件差,仅有一个台式电风扇可用。我平心静气,写了一页又一页,时间不知不觉便溜过去了,哪还记得什么暑热难消?
后来调到文联,庆幸的是单位有一个与天地自然亲近的大院子,常让我有回归乡村之感。尤其喜欢夏天的夜晚,院子里月色皎皎,池塘边蛙声一片,我敞开了办公室的门窗,此时,读书也好,写作也罢,都再惬意不过。
所谓七月,何足惧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