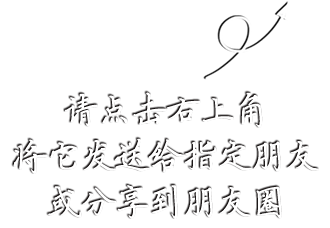落叶凋零 李海波 摄
■ 刘文波
张爱玲说:“戏里只能有正旦、帖旦、小旦之分,而不应当有‘悲旦’‘风骚旦’。”这与我对树木落叶的看法暗合,落叶也不应有“悲旦”“风骚旦”的。诗书典籍里的那些自古逢秋悲寂寥的言说,只能是过多地打上个人的印记,将自己的愁思悲情硬派给落叶,有强人所难之嫌。秋叶飘落无论于视觉还是听觉都应是一场舞剧盛宴,一场华美交响。
当秋风带着远方的讯息飘过树梢,一场大自然宏大的多幕剧便开始上演了。没有主配角之分,每棵树都是天地间的主角。
而不同树的落叶是不一样的。有的如老妇唠嗑,絮絮叨叨,拖沓冗长;有的如大家闺秀出阁,娇娇柔柔,弱不禁风;有的则如壮汉行路,招摇过市,吆三喝四,把地面窗户震得山响。
槐树榆树枣树柿子树的叶子落得快,叶片还未完全变黄,一阵秋风就足以荡尽整棵树的叶子,望秋先陨的就是它们。柿子树叶经了霜,下面的叶子还绿着,树梢的就已由绿转黄,一半红黄,一半深绿,如脂粉未匀,但也好看。等到树顶的叶子掉尽了,底下的还酽酽的绿着。待到叶子落净,剩下通红的柿子在枝头,如炉火,如灯笼,如温暖的呵护,那热闹的颜色,使人觉得天又暖了起来。哎,落叶们着什么急啊。
系出同门的杨树桦树,虽是兄弟,但一个是灰头土脸,老实巴交的庄稼汉,无论生在乡下还是城里,都不改其土气;而桦树则华冠丽服,温文尔雅,一身书卷气。杨树扛不住寒气,叶子落得快,秋风刚刚传话,它们就如在聊天的村妇,叽叽喳喳,一下子想起饭还未做,孩子还在饿着,就没了聊天的兴致,风风火火地各忙各的去了。而桦树则经霜不凋,叶子绿得依旧如翡翠,直到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,方落尽了。
公园里,柳树落叶也晚。与其说是落尽的,不如说是冻掉的。不到零下几度,不到冰剑如戟,就一直瑟瑟地绿着,耐着性子,仿佛能够忍着过冬。而一阵强风寒,温度骤降,被冻干的叶子,一下子冻干失水,有时叶子挂着积雪,依然能挂好几天。柳树是恋秋的。
梧桐敌不过秋霜,往往在寒雨之夜或下霜的凌晨,人已入梦或将醒未醒时分,大片的叶子如累积的盛年心事,倾泻而下,谁都劝不住,一下子全落尽了,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,让第二天醒来的人感到空落落的,不适应。因此,觉得只有梧桐叶落里有更多的悲情在里面。“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,点点滴滴。这次第,怎一个愁字了得。”国亡家痛,身世家愁,在风雨之夜,让李易安感到流年之痛。因此,梧桐很有传统文化里的惺惺相惜之感。
法国梧桐则没有这种感受。浓绿硕大的叶子待到由黄转绿的时候,从树底下往上看,却很能让人浮想联翩。这黄色是浪漫沉稳的。它是枫丹白露的灵光片羽,还是浪漫女神的深情眷顾?这都源于她是法国梧桐。其实法国梧桐应叫做伦敦梧桐的,读安妮宝贝的《童年与树》知道,它其实是在英国培育,只因为从上海的法租界开始种植,便改名易姓,如女子嫁夫随夫了。它的学名其实叫二球悬铃木的,一个很乏味的名字,与浪漫不沾边的。
女贞是经冬不凋的,这让看惯了萧瑟荒芜寒冬的北方人感到有点诧异,毕竟冬天也是有绿意的,除了老气横秋的松柏。这让人另眼相看。她很有松柏的高洁,此外又有着别的树高不可及的精神气在里面。绿色不改,名如其物,女贞的名字看来没有取错。那些早凋的树会有什么感想呢,大概没人知道的,毕竟时代换了,在其他树看来,女贞又有点迂腐,是不是啊?
于萧疏的深秋,秋叶其实是足观足感的。在落叶纷纷的林莽间行走的旅人,心事清癯。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。”大自然的法则是不能逾越的。有“删繁就简三秋树”,才有“标新立异二月花”。天地不仁,实际上是平等博爱的。该生的则生,该灭的即灭,一切由自然的法则公断。其实,让万物以素洁之身去迎接风刀霜剑的严冬,是与万物相亲的。只有身无附碍,方能无所畏惧,捱过严冬。这一点,树比人想得开。人总是用欲念来营巢,拿名利来取暖,结果却是可想而知的。心灵的翅膀过于沉重了,怎能展翅高飞?
“不与夏虫语寒,不与曲人语道。”这句话是淮南王刘安说的。夏虫只暑不寒,曲人心机太重。生命里缺少了必要的言说条件,于寒于道的境界,就已相距甚远了。想想贵为王侯的刘安,常人一定以为除了饱食终日,花天酒地,一定是无忧无虑的。其实,想一想,高祖麾下有多少功臣名将,同姓王异姓王,在政治的煎锅里身首异处,惶惶不可终日。封建王权的机器一旦运转起来,是容不得任何不协调的音符的。对异己的讨伐,就好比自然界的秋风扫落叶一样,没有亲疏情理在里面的。醉心方术,痴迷丹药的淮南王可以让君王安心了。虽然没有炼出丹药,长生不老,谁又不知道醉翁之意是不在酒的。而刘安凭着淮南术无意中发明了豆腐之方,却是能极口腹之欲的,是可以致福的。刘安因此能颐养天年,卒保终身了。
秋叶落尽,一下子高远了,让人可以滤去遮蔽的树叶看一看蒙蔽了很久的天空,大都能想出些什么的。树都想透了,人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