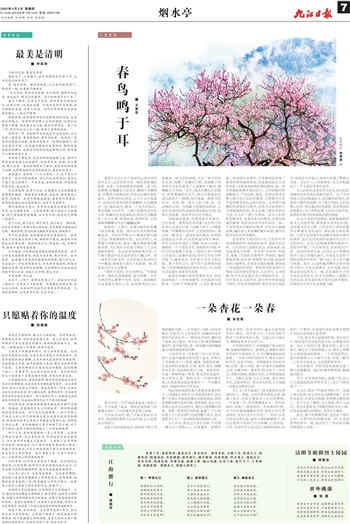■ 李风玲
儿时记忆美,最美是清明。
柳枝长了,小草绿了,村东的那条大河和小河,又听见淙淙的水声了。
风,暖洋洋的。教室里的我,正在老师的带领下,和同学一起,扯着嗓子读课文。
“大兴安岭,雪花还在飘舞,长江两岸,柳树开始发芽,海南岛上,鲜花已经盛开。我们的祖国多么广大。”
读完了课文,又学完了算术,老师带我们排起长队,去村头的一处高地扫墓。队伍不长但弯弯曲曲,我们轻轻地走着,没有人说话。我们非常郑重地走在扫墓的路上,一派庄严肃穆。
扫墓结束,我收拾好奶奶用花布做成的书包,走在回家的路上。班里的男孩攀上大树折柳枝,女孩们就在树下候着,然后各自分几枝,抱在手里回家。第二天一早,将它们往大门上一插,便有了清明的味道。
清明节一早,当我掀开水缸的盖子舀水洗脸,必定会有一棵菠菜,青青绿绿的,漂在水缸里。奶奶说:“清明用这样的水洗脸,能够清神明目。”我那时候很小,但对此深信不疑。我虔诚地撩起水缸里的水,撩起离菠菜最近的那汪,我将它们轻轻涂抹在眼睛四周,感觉整个人顿时神清气爽。
母亲做了荷包蛋,先将煮熟的鸡蛋剥了皮,再用刀将蛋清部分割上四道豁口,然后再烹油、进锅,加上酱油,缀上韭菜。酱油给鸡蛋加了滋味,韭菜则给鸡蛋减了油腻,这荤素相间浓淡结合的味道,最合我的胃口。
盛进盘子,母亲说:“一人必须吃一只,吃了身上不长疖子。”孩子们很快抢食,大人们也没有推让,各自吃下属于自己的那只。平安是福,身体的康健,对贫瘠的家庭来说,意义深长。
吃完荷包蛋,我滑下炕沿,去看锅台上泡在胭脂里的鸡蛋和鹅蛋。鸡蛋染在大瓢里,是红的;鹅蛋染在小瓢里,是绿的。我用手轻轻地拨动,看是否已经着色。我要怀揣着这些彩色的蛋们,去院子里荡秋千。
那时候的院子很小,爷爷却总能在这样狭窄的空间里,打上两根木桩。儿时的清明,除了插在门上的柳枝,除了染在瓢里的鸡蛋,必不可少的,就是院子里那一挂秋千。
挖了土坑,埋了柱子,绑了绳子,挂上板子。那时候,似乎家家都有一块两头有孔的木板,家家都有几根粗粗的大绳。每到清明,它们就被从棚屋里拿出来,搭成秋千。
拿了红皮鸡蛋,我和姐姐在院子里荡秋千。我还约来了住在南大街的小妮,她的胆子很大,她荡秋千的技艺也非常之高。她站在秋千上,带着我一起,手脚并用,把秋千荡得老高老高。
天已傍晌,口袋里的鸡蛋被我摸得有些发烫。很多小孩在玩碰蛋的游戏,但我只是旁观,绝不参与。我不舍得。我捂着口袋里的红鸡蛋和绿鹅蛋,捂了好几天。不过就是一只水煮的蛋而已,不见得多有滋味,但因为澄澈的清明,因为鲜红的胭脂,它就那样扎实地站在我的童年和记忆里,令我久久怀想,挥之不去。
岁岁清明,今又是。
长大了,心野了,世界也变得小了。再在院子里挂一架秋千,已经是不可能的事。还有酱色的荷包蛋,长大成人的我,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母亲当年的味道。儿时的清明啊,让我至今怀想,念念不忘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