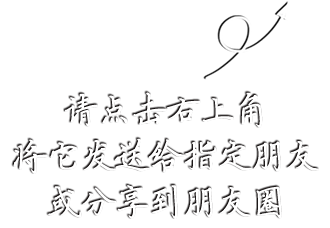■ 米丽宏
那天在客厅读书,忽然“叽叽叽”,一串细嫩的鸟鸣,从窗缝儿钻进来。嘿,不用说,那个老位置又住鸟儿了。
我家窗外空调机与墙壁间那团盘卧的管子,往年春天总会被鸟儿相中,筑巢做窝,安然入住,然后夫唱妇随,生儿育女。
对这不速之客我们都很喜欢。一发现芳邻又至,开窗的动作都变得偷偷摸摸。瞅大鸟不在,就凑上去好好看个够。拍照,发朋友圈,与朋友分享。
前年春天,来的是一对黑灰鸟儿。微友看了照片,说这种鸟叫鹪鹩。它们的羽毛像旧时代男人那种黑不黑灰不灰的大袄,看去真不体面;不过即便这样,它们仍是美的。黑如点漆的眼睛,机巧的脖颈,一枝覆压一枝的羽毛,风中昂头飞翔的姿态……
两只鸟从选址到入住,我一直在关注着:它们拖草背枝啄泥,一趟趟穿梭往来,两三天便筑起了新居。我欣喜地在朋友圈做着现场直播:鸟儿蹲在窝里了,看见一只蛋了,两只蛋了,鸟儿轮流抱窝了。终于有一天,小鸟儿破壳了。三只!
哎呀,丑得呀!它们几乎是赤裸裸的“肉滚子”,头尾扎煞着几根毛,浑身通红,不能站立,紧闭双眼。一缕阳光斜照,它们的身体竟然半透明,里面进行着复杂的蠕动。
我用手指头逗逗它的嘴,它居然张大了嘴巴!它的喙坚硬,同时又很柔软,一圈儿黄边儿,红色大口直抵内腔。它摇晃着,仰头接食儿,无所防备,无所顾忌,坚信上面便是它们的娘。
一种神奇的感染力直抵内心,为这种信任,我心里无端生起一种柔情。
一个暴雨天,大鸟迟迟不见回来,没长全羽毛的小鸟儿被雨淋得瑟瑟发抖。我东寻西找,找了一块三合板,盖在外机上,给它们挡雨。那天鸟再也没回来,后来小鸟儿也消失了。我们疑虑重重:是大雨中遭受意外,还是鸟儿全家搬离了?
我心里不安了许久,终于有一点心得:万物都有生存之道。鸟儿是爱自由的物种,不可干预;以一己之心去猜度鸟心,难免帮倒忙。
今年,鸟邻的照片发朋友圈后,微友说是花翎。漂亮是漂亮些,但它们更敏感,人影一晃,窗帘一动,便“忒儿”一声先后飞走;害得我们在客厅里,整天小心翼翼。看看大鸟儿飞走,才开窗;晚间,关窗拉帘子,都像做贼一般。
有一天,女儿回来,我告诉她,有鸟在窗外筑了巢,孵着小宝贝儿呢。女儿一喜,跑去“唰”地拉开了窗帘,大鸟“忒儿、忒儿”先后惊飞。
一晚上偷看了好几次,都没见大鸟回来;心里只叹不妙。
我们埋怨女儿莽撞,事到如今,怨也晚了。我嘟囔道:唉,终究是鸟儿,你对它多好,它都不懂。
我老公说:也怪不得它们啊,它们大概不信任人类了。每天,有多少人举着枪,张着网要捕获它,等着吃美味佳肴。眼下,树林子越来越少,它们建个窝都没地儿。
我女儿说,有天在市里一家饭店吃饭,点菜时,竟然有“绿林布谷”。服务员说,就是清炖布谷鸟!哎呀,小时候在老家听它唱“割麦种谷”,真不敢吃呀!
唉……可是,现在不“敢”吃的人,越来越少了。
我说起,小时候小伙伴爬到高树上掏鸟窝,村里老人见了,常要拦着。有个老太太一看见就撇嘴长叹:“作孽呀,作孽呀!放了它吧,一家子活物哩!”我们觉得好笑。现在想想,真是罪过。有时掏了鸟窝,大鸟看见,拼命扑上来啄。有次,把二嘎的耳朵啄了个豁儿。是我们毁了它的房子,抓了它的子女,它痛心愤怒啊,它肯定会诅咒,人啊,你毁了我们,你们也会毁了自己!
……
那天,两只惊飞的鸟儿,什么时候回的,我留心观察还是没看到;但夜半,轻轻掀起窗帘一角,看到了俯卧其中的鸟,心里阴霾被清风拂去,真是妥帖啊。
半月余,窗外小鸟儿已满披了羽毛。它们见母亲一回来,便一片儿声尖叫,嫩声细气,如一堆儿小孩儿。居家安暖的温馨,不过如此啊。
最近,我又去“偷窥”了一次,小鸟已有了分辨能力。见我凑近,它们羞怯地把头缩下去,缩下去,收紧了翅膀;而鸟妈妈回来,它们便伸长了脖子,叽叽叽叽,叫成一片,又娇憨又放肆。
鸟邻入住的夏天,我们客厅里的空调基本会成为摆设。我们开着风扇吹风儿看鸟儿,一个“偷窥”的夏天,饶有风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