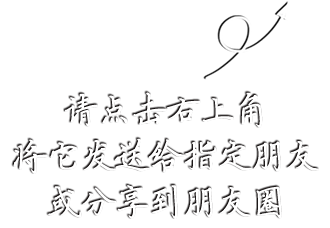■ 李迎春
那是某个初夏很寻常的一天,当我在花店角落第一眼看见它时,就惊诧于它的张扬与恬静了。蓝紫色的花球挤挤挨挨,开得热烈铺张,像一群穿着蓬蓬裙的少女。花店主人正用喷水壶给它洒水,水珠在花瓣上时走时停,最终坠入花心。整株花儿倚在墙角美丽而又安宁,恰如《诗经》中那个“俟我于城隅”的少女。
“这叫无尽夏”店主甩着喷壶说,“能从五月一直开到霜降。”听到这个名字颇觉新奇,心下想:不就是绣球花吗,咋就叫了个这么古雅的名字?我忽然想起杜拉斯《情人》里那个“十五岁就老了”的少女——有些生命,注定要在最盛时被赋予沧桑的名字。我的私心里常有一种偏执,总以为:爱花的人,一定都是诗人,或者说,至少有诗人般的多愁善感,他们总爱给花取上诗意的名字,引人遐思。譬如,耳熟能详的绣球花竟被冠以“无尽夏”,念在口中,音韵和谐,且眼前满目葱茏。
这“无尽夏”的名目,倒也别致,仿佛将整个夏季都囚禁在那团蓝紫色的花球里了。
我掩饰不住对它的喜爱,忙不迭买回一盆,搁在朝北的窗台上。北面的阳光是吝啬的,只在清晨时分,才肯施舍些许微光。然而这花竟也不挑,兀自生长起来。先是嫩绿的芽,继而舒展成肥厚的叶片,边缘带着锯齿,像是谁用钝剪刀随意剪出来的。约莫过了半月,枝梢上悄悄地冒出几个青豆般的苞。
仿佛是得了那几个花苞的鼓舞,我更是日日精心侍弄,那苞便一日日膨胀起来,终于在一天清晨,“啪”的一声,花苞,绽开了。初放时是淡绿的,渐渐染上蓝紫,最后竟成了深沉的靛色,花瓣边缘却又镶着一圈白,如同被月光吻过似的。这花确实古怪。同是一株,今年开蓝花,明年或又转作粉红。带着好奇上网查了资料才知晓,原是泥土的酸碱性在作祟。酸性土生出蓝花,碱性土则生粉花。我想,这花倒是个随遇而安的性子,环境给它什么,它便接受什么,不似某些花木,稍不如意便萎蔫给你看。
正如花店店主所说,花期确是长久的。从五月一直开到十月。花朵老了,也不肯轻易凋谢,只是颜色渐渐褪去,成了枯黄,却还固执地挂在枝头。我有时看它,竟觉得那不像花,倒像是某种不知名的生物,正用无数小眼睛窥视着这世界。
邻家小朋友正读小学,时常爱踮起脚趴在窗台,鼻尖抵着玻璃看它。一次他稚声稚气地问:“这是什么?”待我炫耀似的答之以“无尽夏”时,他便睁圆了眼:“夏天不是会走吗?”童言如镜,照见这名目的荒诞。人类总是这样,极愿意给易逝之物冠以永恒之名——将初绽的玫瑰唤作“永恒之爱”,把薄暮的霞光称作“不夜天”。这绣球花又何尝不是承载着人对夏日的贪恋?明知四季更替不可违逆,偏要在唇齿间将季节囚禁。
昨夜一场暴雨,今晨看时,那花球已被打散了大半,残瓣黏在泥土上,像是谁随手丢弃的碎纸片。然而枝头又有新苞在孕育了。原来所谓“无尽”,不过是旧的花谢了,新的花又开。如此而已。
人们执着于“无尽”,或许并非真的妄图对抗自然规律,而是在有限的生命里,寻找对抗虚无的锚点。旧花凋零、新苞孕育,看似轮回重复,实则每一次绽放都是生命对时光的全新应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