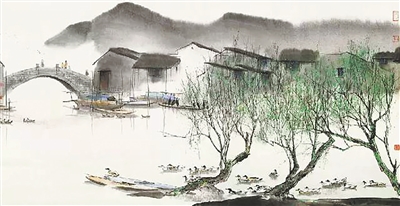■ 卢小澍
家乡在赣西北大山里一个叫铺里的小自然村,之所以叫这个名字,可能是因为之前所在行政村的“商业中心”——杂货店在此。铺里的老房子依河而建,是青砖青瓦木门窗的明清建筑,屋连着屋,家挨着家,采光靠天井。家门口的河上有座叫纱笼桥的老桥,是铺里人的“CBD”。
老桥东西走向,建于清同治十年(1871年),宽5.4米、长24米、高8米,3个青石桥墩(东、西引桥各1个、水中1个)上安放木梁,上铺木板,木柱支撑小青瓦顶的9节桥廊,两侧有木栅栏和木凳,砖砌东、西桥门,是以前修水通往湖北的要道。老桥旁边有一棵高过桥的大桑树,据说树龄过百年,桥下是一条深山里流出来的小河,河面宽的地方有十来米,最深处近两米,儿时最开心的记忆大多与桥和桥下的河有关。
天边的晨曦刚刚亮起,就有拿着柴刀、扛着锄头、牵着牛的村民从老桥上经过,干活趁早,早上要凉快一些。稍晚一些,桥上就是三三两两去上学的学生,村里的学校,离桥有好几里路,要早些出发。偶尔有几个飞奔而过的,书包在背上啪啪作响,多半是贪玩误了时间怕挨老师罚的。
傍晚,夕阳透过栅栏,落在桥面上,留下一条条金色的斜影。老桥上的人多了起来。农忙回来的,在桥上小歇,收收汗,聊聊最近的收成,说说家里不争气的孩子和邻里那些永远理不清的糟心事。孩子在桥上玩耍打闹,等着炊烟升起后回家吃饭的召唤声。还有些远方的赶路人,也会在桥上吃吃干粮,补充体力。
夏天,是老桥最热闹的时候。以前的乡村,没有电,更谈不上电扇、空调,所以找地方乘凉是每天必做的事情。老桥桥墩高,桥两侧的河岸也高,河风大,穿桥而来的风掠过身体,异常凉爽。中午是最热的,有些人早早吃完中饭,到老桥的木凳上找个靠桥廊的地方躺下,在凉风中美美睡去。有些干脆端着饭碗,到老桥来边吃边聊边乘凉。孩子们是最喜欢凑热闹的,有的在老桥上打石子,石子都是在河里精心挑选出来的,色泽大小规整、表面光滑,打石子共10关,先完成的算赢;有的围成一圈,在桥面上玩纸牌,纸牌数字都快模糊了,但是他们依旧玩得不亦乐乎;羞涩一些的女孩,则乖乖坐在父母身边,听大人说着大人的事。
夜幕到来,老桥上就一座难求了,不仅铺里人去,周边自然村的也会去。来得早的,坐在桥靠东边风大的地方,来晚了,就只剩下西边风小的位置了,再晚点,就没座位了。晚上算是乡村最悠闲的时光了,农活忙完了,也不需要辅导作业,有的是时间去拉拉家常、聊聊村里那些趣事,在家待着还费煤油,老桥自然就成了最好的去处。农村人起得早,睡得也早,9点以后,人会慢慢退去,深夜了,偶尔会有几个在桥上睡着的单身汉,等着自然醒。
对于孩子来说,老桥还有一个用处,就是下河戏水的召集地和休息地。下水之前,到老桥集中,领头的说走,便一窝蜂地往河里冲。铺里的孩子们一天要下水三次,上午10点和下午3点是瞒着父母去的,下午5点算是洗澡,可以正大光明去。农村没有什么防暑降温措施,冰棍可能半个月才有镇上的人来卖一次,要父母在家、心情好才有可能品尝一回。对大多数孩子来说,冰棍是奢侈品,下河戏水才是“正道”。顶着烈日下水,其实伤身体,也容易晒黑,但是农村没有什么游玩项目,父母也懒得花大力气去管,偶尔心情不好了,抓来揍一顿。铺里的孩子,没有不会玩水的,没有人教,自己跟着大孩子学,什么狗刨、蛙泳、仰泳、潜水,虽然不如现在城里孩子的姿势标准,但是大体都会。
孩子们在水里追逐、击水,比谁潜水时间长、比谁游得快,累了就爬到桥墩下岩石上,喘口气做个很帅的动作往水里跳,调皮一点的,从河边挖一把泥,涂在脸上,做个很夸张的表情,大叫一声,再往水里跳。玩水的时候是开心的,时间过得也快,孩子们也不敢在水里太久,要趁被父母逮到之前,回到老桥上,等待下一次下水。
在老桥上,可以观察河里孩子们的一举一动。记得有一次,一个两三岁的孩子,本是在河边浅水处看哥哥姐姐们玩,估计是看入迷了,一步步往深水里走。被在桥上看风景的一个小堂叔发现了,拔腿就往桥下跑,把小家伙抱起来了,好在时间短,小家伙就喝了几口水,没啥事。小堂叔其实比我年纪小,当时也就十来岁,算是半大的孩子。自我记事以来,老桥下从未出现过溺水伤亡事件,算是万幸的。
因为年代久远及艺术价值等原因,2018年3月9日,老桥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重新进行了粉刷修葺,比以前更壮观了。离开老家快30年,每每回去,都要去老桥上转转,桥的两边盖起了不少楼房,紧挨着还修了一座过车的公路桥,河的上游据说开了养猪场。桥下的水浅了,没那么清亮了,桥上的风好像也小了,少了儿时的清凉,桥下戏水打闹的孩童不见了,桥上纳凉的人也没了,偶尔有几个老人从老桥慢慢穿过,没有任何停留。
老桥,现在就只是桥了。